写于20221205,我转载于20230215。
我生来就是个丑八怪。
我仅仅因为外貌,就遭受到了非人的歧视。
他们把我脸上长的瘤子刺破,他们把我相比左眼显得太小的右眼打得肿胀不堪,他们用强力的晾衣夹夹住了我的过大的鼻孔,用胶带封住了我厚厚的嘴唇。
多么可笑。
我自己身上的器官,明明能够正常地行使它们的功能,仅仅因为它们不符合某种特定的比例,仅仅因为它们让他们感到不适,他们就有权修改它们在我脸上的排布。我的器官,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需要别人来告诉我,我的器官该怎么排布才让他们舒服。仿佛我的眼睛不是用来观察事物的,而是用来被凝视、端详、找乐子、供他人获得视觉愉悦感的;仿佛我的鼻子不是用来呼吸空气的,而是用来被凝视、端详、找乐子、供他人获得视觉愉悦感的;仿佛我的嘴巴不是用来诉说我的痛苦、进食、获取能量的,而是用来被凝视、端详、找乐子、供他人获得视觉愉悦感的……
凭什么?凭什么他们的愉悦需求建立在了我的生存需求之上?凭什么我自己身上的器官不优先为我提供生命保障,而是优先为别人提供视觉服务?
脸上的瘤子被刺破,流脓感染,更加引起了别人的不适。带头霸凌我的那个男生满脸横肉,凶恶地狠狠踢了我一脚。我吃痛,抬起头看了一眼,牠的脸也是通俗意义的丑,长期的条件反射使我一看到牠的脸就生理性地想吐,我恐惧牠的脸,牠的脸令我感到不适。
我脸上流脓了。黄色的浆液粘到了横肉的鞋底上,牠一看,嘴巴歪到了脸外面,又狠狠踹了我一脚解气,叫上了几个跟班把我拎到工具间,砰地一下甩上了门。
工具间里很黑。我在不停地思考着,脑子像一台不停运作的毛线思想发生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毛线一般的思维,再绕到一起,偶然碰撞出一些东西。
毛线思想发生器冒烟了。我猜想是脸上流脓感染了,我开始发烧,意识模糊。
一个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
他们霸凌我是因为我丑吗?我如果漂亮了,他们就不会霸凌我了吗?丑的本质是什么?美的本质是什么?
横肉脸丑吗?为什么横肉脸还是有那么多跟班?为什么没人羞辱横肉脸丑,没人以牠丑为由霸凌牠?
丑的本质是五官排布不规律吗?是令人感到不适吗?横肉脸也让我感到不适,普遍意义上长得漂亮的另一个男生的脸也令我不适,因为牠也霸凌我,牠们的脸都在我脑海中形成了条件反射,我一想到就会不适,牠的脸让我不适了,在我的视角中牠为什么不能称作“丑”?
美的本质是五官排布符合一定的规律吗?是令人感到愉悦、舒适吗?我要是真的“美”了,他们就一定不霸凌我了吗?如果美的本质就是令人感到愉悦的话,美丽的我不被霸凌是否仅仅是因为牠们舍不得破坏牠们的愉悦感来源?我变美了,是不是也无法伤害到牠们,恶心到牠们,只会如了牠们的意,因为牠们霸凌我就是因为我无法给牠们提供视觉愉悦感?
那相应的,我的丑是不是成为了牠们的不愉悦感来源?如果我拥有了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力量,即使我的外貌让牠们不适,即使我的行为让牠们不适,即使我的人格让牠们不适,牠们还敢欺凌我吗?
我明白了。
原来根本上,我不是因为外貌让牠们不适而受霸凌,而是因为我没有权力。
我要报复。我要逆袭,血债血偿,我要用我外貌让牠们不舒服、恶心、恐惧、害怕、哀恸、痛哭、求饶,正如牠们用行为让我不舒服、恶心、恐惧、害怕、哀恸、痛哭、求饶一样。
我不要漂亮,我不要用愉悦感满足牠们的需求,我不要胆怯地用肉投喂因饥饿尾随我的野狼,畏畏缩缩地有求必应,满足它们提的要求;我要直接让它们不适、让它们胆怯,我要猎狼。
我要权力,我要力量。
黑暗中,什么东西感受到了我波澜壮阔的情绪,悄悄在无穷无尽的暗影地带凝结出了实体。它挨上了我的脚尖,凉丝丝,冰冰凉,像黄昏后的湖水。俄顷,它爬上了我的大脑,和我融为了一体。
我感到,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帮助我,我有力量了。我兴奋地舔了舔裂成两半的嘴唇,有什么东西觉醒了,有什么东西被我丢掉了。
有力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塑我的外貌。作为一个未来的邪神,我当然希望自己越恐怖、越“丑”、越吓人越好。
我给自己安排了九百只眼睛,因为它们首先是我的器官,首要作用是为我带来良好的视野、观察外界,所以当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古神的力量似乎也不能让我突破质量守恒定律,为了安下如此多的眼睛,我不得不把自己的躯体变成了一摊肉泥。黏黏的、腻腻的黑棕色半流体从属于人类的衣衫中流下,蠕动出来,欣喜地接受着自己的新形态。“啵、啵、啵……”一只只眼球像花一样竞相在我的躯体上开放,骨碌碌地转动着。我感觉好极了,我现在能同时看到九百个不同的方向的景象。不过,要同时处理如此多的信息,人类的大脑似乎不太够用。于是粉色的组织疯狂增长、蔓延,体积扩大到了原来的四倍以上。我思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敏锐过,一小时前还困扰着我的难题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像幼儿园习题一样好笑。大脑很脆弱,古神的力量也有一定的限制,我不想透支她的力量,所以我需要提前先做点儿措施,保护好我的眼球和大脑。怎么保护呢?人类的骨骼已经没什么用了,我用我的再生胃把它们全部融化,再塑成了一层坚硬的壳,套在我的大脑外面,皮肉里面,神经从细密的孔里链接大脑和肌肉。至于眼球,我希望有透明的壳,但人类的骨骼可不能变成透明的。于是我拿一部分骨骼长了更锐利的牙,吞下了一些工具间里的玻璃制品,我的眼睛外面就覆盖上了一层钢化玻璃。为防止不必要的弱点,我自主切断了一些大脑里的痛觉神经,尤其是眼球的。
什么能让人类感到恐惧呢?我作为一个曾经的人类,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恐惧和厌恶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很相似,区别在于人们对于没有力量的事物厌恶,对于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事物恐惧。我调用曾经头发里的色素,在自己的外皮肌肉上显示出了密密麻麻的斑点,是能最大程度地引起密集恐惧症的程度;噢对了,相当一部分人害怕人脸,恐怖谷效应对于制造恐惧也十分有效,我随机在密集的斑点之间穿插了几张不符合常识的人脸,有的用鼻子对你微笑,有的长了狗的牙齿,有的长了海豹的眼睛。还有重头戏——曾经的他们不是很厌恶我吗?我现在明白,一旦他们意识到,本就被他们厌恶到极点的我,变得如此恐怖又有力量,他们的厌恶会加倍地转化成恐惧。我在宽阔的大脑内轻松地找到了我作为人类时的相貌,精准地、原封不动地还原到了我精心捏好的一团皮肉上。那其实并不是我的头,里面没有大脑,刚好还能对愚蠢的人类们起迷惑作用。
有九百只眼睛,当然也有许多耳朵。我在每一个斑点后面都安排了一张感受震动的薄膜,大概相当于人类概念中的耳朵吧。现在它们听到横肉脸来了。
横肉脸怎么会来呢?怕我真的死了负不起责(虽然作为人类的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死了)?还没打够,想再多揍我几拳出气?作为一个没有想通“美丑”本质的肤浅人类,被别人骂“外貌让人感到不愉悦”了,所以想来看看我,证明自己外貌并不是如此地让人不愉悦?
我的大脑觉得人类真可笑,怎么就是想不通呢?为什么横肉脸不为自己的行为让别人感到恶心、不舒服而感到羞耻、自卑,却会为自己的外貌让别人感到恶心、不舒服而感到羞耻、自卑呢?
恶心、厌恶与恐惧本就是一回事儿,不过就是被恐惧的对象权力感更大,而恶心与厌恶带着居高临下的轻蔑罢了。
这么想着,我知道我要让横肉脸感到恐惧了。刺眼的光线照射进来,感受光的九百只真眼闭上了一大半,可是那张令人生厌的脸上的一大一小两只假眼却仿佛感受不到光似的,不仅没有半点闭上的迹象,还用楚楚可怜的眼神望着横肉脸。横肉脸小得可怜、只有我四分之一大小的大脑接受到这一信息,疯狂地向低等的人类身体发送信号,下丘脑赶工,拼命要求机体分泌肾上腺素,然后,我只是用假眼和牠对视了一眼,牠就倒下了。甚至不用我自己出手。我的敏感的神经感受到,牠已经没心跳了。
我愈发感到我的论断是正确的。如果我只是选择把自己变得很漂亮,可不能把牠美死。再说了,我为什么要让我的仇人幸福地去世?
我像只快速的蜗牛一样,从工具间里爬出来,享受人们的恐惧与尖叫。因为那意味着,牠们怕我,我有权力,我有力量,我根本不用自己动手,仅仅是在那里趴着,就能让我的仇人们感到痛苦——还有比这更酷的事吗?
我路过横肉脸的尸体,雄性的臭味令我感到不适,我把这视作一种对我的冒犯,随手分泌酸液把它溶掉了。关于性别,这倒是提醒了我,我把我的子宫融合掉,只剩下卵巢和输卵管。胎盘最开始本就是一种病毒,哺乳动物带给雌性数不尽的痛苦,我作为一种全新的物种,把自己改造成了卵生动物。我更原始,更自然,更接近那位古神了。
我心情愉悦,故意慢悠悠地爬过工具间到教室的走廊,以便让更多的我的仇人感到痛苦。数不清的学生、老师开始捂着眼睛大喊大叫、闭眼到处跑、互相撞翻撞倒,我未曾主动发动任何攻击,牠们自就乱成一团。
随着倒下的仇人变多,我感到我的力量也在慢慢增强,层次在变高。我发现我似乎拥有了在不同的人面前,呈现出不同的样貌的能力。毕竟影像就是光子通过视网膜传递给大脑的信息,我似乎变成了更高维的存在,本真的我已经超脱了这个小世界,我看到了一些真理——比如我只是一篇小说里的主角之类的。本真的我存在于更高维的空间,我在这个世界的投影自然可以千变万化,投影投到每个灵魂的视网膜上的图像当然也可以不一样。
我感到欣喜,因为这意味着,那个没有因为我被动而平等地让每个人感到不适而霸凌我的女孩,那个和我同病相怜,报团取暖的女孩,能够得到我的奖赏——是的,在我的价值观当中,我以古神的恐怖形象出现,是对你的惩罚,或者说是我的本分,你没有我有权力,你没有我有力量,你只能忍受;但是我喜欢你,我认为你的行为或你的人格让我感到愉悦,那么相应的,我会以让你感到愉悦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作为对你的奖励与礼物。
我的过于发达的大脑不到一秒就迅速构思出了一个极为宏美的形象——严格按照斐波拉契螺旋线生长的海螺、严格按照黄金比例迭代的几何图形、四维空间的超立方体、包含并压缩了世间万物的点……总之,每一个元素都按照智慧生物大脑对于美的最高理解安排,塑造出了一种极为超脱、雌伟、宏大的美。这种因为契合了自然规律而产生的愉悦感和人类的繁殖欲、审视同类产生的愉悦感相比,如同地球与一粒尘埃。每一个智慧生物都能感受到前者之美,而只有人类才能感受到后者之美。
我决定就以这个形象去见她。我的本体顺着这个世界的走廊爬到高三(1)班的教室,感受到了里面的语文老师在念男文学家钱钟书的名言——“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下面的学生们哄堂大笑,都觉得这名人幽默极了,他的名言对极了。我用浑浊、低沉、野兽般的音色在里面每个人——除了她——的耳边呢喃:“不。对于真正有权力的人,美是一种对别人的奖赏,丑是一种对别人的惩罚。过度地强迫无辜的人细看自己丑的样貌,是对无辜的人的残忍。”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我看着里面的人类们像一群鹌鹑,有的难以置信、有的捂耳朵、有的尖叫。
而她,正在等待老师同学借此话题,阴阳怪气、内涵自己的她,听到的是一个清脆、铿锵、悦耳的声音:“我是野草,我回来了。”从高维传达过来的语音,即使声音不再是我原来的音色,但她仍可以通过语调判断那是我,我真的回来了。
我操控在这个世界的化身进入到教室,分泌了一种酸液强行融化了牠们的眼皮,分泌一种粘性液体固定住了牠们。与此同时,我带她离开了这个没有人类爱她的世界,把她拥到了我高维的本体中,她可以在那里,我身体的内部,看见会让所有智慧生物感到愉悦、震撼的美。
此时此刻,曾经霸凌殴打我的仇人们身处恐怖的炼狱,被迫尖叫着观摩我的身体作为LED显示屏给牠们播放人类的大脑绝不能承受的猎奇画面;我爱且爱我的女孩被愉悦感的天堂包裹,看着充满了智慧的自然规律给她的大脑做按摩。
我给以前那个叫自己野草的人类和以前那个叫自己树根的人类复了仇。令我的神经感到痛苦的、分别杀死我作为人类的每一部分的、助纣为虐的,一个都逃不掉。
我把意志从那个世界的化身收回来,那个世界的化身从此就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畸形怪物,任凭它拥有发达的大脑,灵魂的抽离也使得大部分神经失活了,没有什么自我意识。人们害怕看到它,一旦它出现在人类的视网膜上,人们轻则恶心尖叫呕吐颤抖,重则当场死亡。人们发现他们怎么也杀不死这怪物,皮厚筋韧,样貌又恐怖异常,造成大规模恐慌,于是某一年,人们合资,一致决定把它送上了外太空。后来这具化身在外太空受到辐射,发生变异,孤雌生殖,产下了很多卵,成为了一个新的种族的母体,这又是后话了。
我把古神的力量匀了一半给她。她狡黠地告诉我,这股力量她很熟悉,最开始,就是来自于她捡到的一块闪闪发光的碎片,像星星,像心脏。她把它藏到了工具间,我们平常挨打的地方。
后来呀,我们一起当了几千年的恶魔邪神玩玩儿,因为外貌受欺凌的女孩只需要献祭三根野草,三根树根,就能成功召唤到我们。当然,我们不会帮她解决外貌问题,只会给她能够解决带来问题的人的力量,毕竟我们是邪神嘛。我们还到更多维度的平行宇宙去旅游,随机在因为外貌霸凌别人的人的视网膜上印一个我的化身的相貌,无论看哪里,即使闭上眼睛,也甩不掉。
再后来呀,我们受益于星星,又回归到星星,又融化成了流动的文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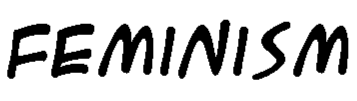

1 条评论
“Lcarus堕海中”的评论:
我好爱这张图。
你说的暗淡丑陋,全部是你的欺侮霸凌。
你讲的仁义道德,不过是你的饕餮盛宴。
我的无知,是因为失权,而非我看不清世界。
你的睿智,是由于当国,而非麦子不能食用。